放客爵士No.1鋼琴手郝瑞斯‧席佛Horace Silver
……Simplicity is very difficult, you know.--郝瑞斯‧席佛接受美國公共廣播網主持人Ben Sidran訪問時,如此說道
一九八五年夏天,剛結束在報社實習工作的我,偕同三五好友坐平快火車出遊,目的地是福隆。沿線經過與數字相關的有趣站名:五堵、七堵、四腳亭、甚至三貂角(西班牙人命名為 San Diego ,台語發音是「三貂角」,它就是台灣中央山脈的起點),最終在福隆小站落腳。
出了車站後,一眼望去,街頭是簡陋的雜貨店與撞球場,原本應是旺季時節,福隆卻因進入民俗月而顯冷清。進入福隆海水浴場內,海灘旁有陽春的通舖間與佈滿細沙的沖浴室。然而,這一切都不減我們狂歡的興頭。就像所有自詡成熟的年輕人,帶了高梁酒與水果罐頭,我們在盛夏時分喝下了最甜卻也最濃烈的回憶。
彼時年少的我,穿著背心短褲,就在萬里晴空的福隆海邊,無畏地曝曬於溽暑驕陽之下。偶有微風吹來,旁邊點綴著稀疏泳客,海灘旁服務處上方的擴音器,不斷地重複播放那一年在台灣走紅的舞曲「 Fresh 」:
議論紛紛這首曲子收錄於一九八四年「 Emergency 」專輯,由當年十分走紅的黑人樂團 Kool & the Gang 所唱。當時的我,雖然不知道「節奏藍調」( rhythm & blues )或「摩城之聲」( Motown Sound )是什麼?但對這種輕快又律動感十足的音樂,我一點都不陌生。這是因為家裡有一堆「朝陽」、「光美」的盜版唱片,全是不同時期告示牌排行榜精選,收錄了 Bee Gees 、 Donna Summer 、 Earth, Wind & Fire 、 Marvin Gaye 等人的作品,而我早已不知聽過多少回。
Conversation is going 'round
人們說著那一位來到城裡的女孩
People talking 'bout the girl who's come to town
可愛又漂亮的小姐
Lovely lady pretty as can be
沒有人知道她的姓名,她是個謎
No one knows her name she's just a mystery
我可能只看過她一兩次
I have seen her maybe once or twice
可以確定的是,噢,她實在棒透了
The one thing I can say is oh she's very nice
她就是我想認識的那種女生
She's a lady one I really want to know
不過我得直接表明才是
Somehow I've got to let my feeling show
「 Fresh 」一曲,延續了七○年代那種我極為熟悉但又很難形容的風格:電貝斯與鼓互為搭配,銅管樂器演奏著重複的樂句,簡單的旋律與節奏,整首曲子清新且歡樂,搭配夏日的陽光、藍天、大海,實在對味極了!
彷彿之間,海灘上所有的泳客都跟著擴音器傳出的旋律,唱著「 Fresh 」的副歌:「 She's fresh ! Exciting ! She's so exciting to me !」每當唱到「 fresh 」這個字時,旋律上揚帶出了輕巧的跳躍感,主唱以假音來點綴歌曲的氣氛,那種舒暢快活,搭配著七○年代末風靡一時的迪斯可節奏,與強烈的紫外線在皮膚上造成的嚴重脫皮,構成了我大學時期最難忘的盛夏回憶。
一九八五年最紅的台語歌是俞隆華填詞作曲,陳小雲唱的「舞女」,國語歌則是陳復明作曲,陳克華填詞,王芷蕾唱紅的「台北的天空」。當年的告示牌年終冠軍是英國 Wham! 主唱喬治‧麥可( George Michael )的抒情曲「無心的耳語」( Careless Whisper ),才華洋溢的 Prince 與落翅仔打扮的舞者 Madonna ,則是美國流行歌壇的兩大巨星。地處於太平洋另一端的台灣,當時還沒有衛星電視這種玩意,自然也沒有 MTV 頻道,流行腳步不免遲了美國半年,這就是為何在前一年就已經大大走紅的 Kool & the Gang 的專輯「 Emergency 」,要到八五年以後,才在台灣某些角落流行起來。
許多年後,出於強烈的懷舊感,將 Kool & the Gang 的精選集買來聽,將它不同時期的暢銷曲複習了一遍,才赫然發現,原來 Kool & the Gang 是一個披著流行舞曲外衣的爵士團體!原名「 The Jazziacs 」的 Kool & the Gang 創團成員貝爾斯兄弟( Robert & Ronald Bells )是五○年代出生的戰後嬰兒潮世代。貝爾斯兄弟的父親是現代爵士樂最重要的作曲家瑟羅尼斯‧孟克( Thelonious Monk )的舊識,也是個狂熱的爵士樂迷,自然影響了兩兄弟對音樂的喜好。作為排行榜上常勝軍的 Kool & the Gang ,成功的秘訣就是延續爵士樂 hard bop 風格慣常使用的和弦配置(由藍調與福音詩歌而來)與活潑的律動感,在編曲時,將這些元素進一步地簡化,讓曲子少掉 bebop 的炫技與複雜度,而用加強重拍的方式來滿足年輕人喜好舞曲的胃口。
當我聽著 Kool & the Gang 演奏「 Street Corner Symphony 」一曲時,察覺到曲子快要結束時,薩克斯風手將 John Coltrane 詮釋「 My Favorite Thing 」的前幾段樂句的方式「裝」進曲子中,貝斯與鼓一樣地製造著固定的重拍,直到結束。這樣欲言又止,保留一手的演奏方式,讓我突然理解,我對於爵士樂的喜好絕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因為在我成長的七○年代中,不論是迪斯可、靈魂、放客、節奏藍調 … 不管音樂類型如何被定義或貼標籤,不論它是草根還是都市化,唱片選曲有無經過盜版商無情的過濾 … 回顧過往的聆聽經驗,我,從來沒有脫離對於黑人音樂的喜好啊!
一直到了二十一世紀,我主要聆聽的音樂類型,反而回溯至前一世紀,一九五、六○年代的現代爵士樂了。這倒不是懷舊感作祟(畢竟那不是我成長的年代),而是五、六○年間,大部分由獨立廠牌所發行的現代爵士樂專輯,對於後來的(特別是黑人)音樂走向,無論流行或非流行音樂,影響實在太大了。在這裡,特別值得介紹的,就是被歸類為「放客爵士」( Funky Jazz )重要鋼琴手的郝瑞斯‧席佛( Horace Silver )。
爵士樂迷對於席佛的作品並不陌生。這是因為席佛最重要的專輯都在知名爵士樂廠牌「藍調之音」( Blue Note Records )旗下發行,而其中最著名的「 Song for My Father 」,不但是個人創作顛峰期的代表作,也是藍調之音六○年代最暢銷的專輯(另一張是風格近似,由小號手 Lee Morgan 掛名的「 Sidewinder 」)。八○年代中期,「藍調之音」捲土重來,除了錄製新專輯外,更展開大規模的爵士經典盤 CD 重發計畫,「 Song for My Father 」被選為「藍調之音」二十五張最佳專輯之一,席佛的作品叫好又叫座,由此可見。
然而,若只聽「 Song for My Father 」來評斷席佛,未免就低估他的作曲實力以及對於打造「藍調之聲」( Blue Note Sound ,泛指在老闆 Alfred Lion 監督之下的廠牌專輯音樂風格)的貢獻了。早在故鄉附近的 Hartford 城(位於康乃迪克州)酒館演出時,席佛就已經是一個優秀的作曲與編曲家,他獲得薩克斯風手 Stan Getz 的賞識,整組三重奏隨 Getz 巡迴演出一年。有心人不妨找 Stan Getz 在 Royal Roost 廠牌發行的「 Chamber Music 」、「 Split Kick 」等專輯來聽,就可發現早在五○年初期, Stan Getz 就已經演奏過多首席佛的作品。
作為與「藍調之音」簽約最久,可能也是最受歡迎,最大牌的鋼琴家,席佛絕非浪得虛名。他的鋼琴彈奏技巧紮實,靈活又充滿節奏感,一方面繼承現代爵士鋼琴手 Bud Powell 的 bebop 語彙,另一方面向福音詩歌與家鄉民謠(席佛有西非維德角群島的血統)借火,發展出律動感強烈的音樂。越是深入聆聽席佛在「藍調之音」的作品,越能深入體會他的音樂魅力。以他在「藍調之音」發行的第二張個人專輯「 Horace Silver Trio and Art Blakey-Sabu 」為例,原本應有薩克斯風手 Lou Donaldson 參與,卻因 Donaldson 的缺席,而變成三重奏的錄音。製作人兼老闆 Alfred Lion 聽過錄音後,極為欣賞席佛高超的彈奏,因而發行此張專輯。「 Horace Silver Trio and Art Blakey-Sabu 」專輯中的每首曲子都不長,但席佛流暢地使用現代爵士樂中的 bebop 語彙,行雲流水的彈奏中,以大量的半音製造一種「暗色」的聲響,搭配 Art Blakey 或 Sabu 波浪式的猛烈擊鼓,可說是爵士樂三重奏的典範。
然而,席佛真正受到樂迷矚目,是他與鼓手 Art Blakey 共同創設了影響爵士樂風格深遠的「爵士信差」樂團( The Jazz Messengers )。這是因為自 bebop 樂勃興以來,樂手已經習慣在酒館作大量的即興演出( jamming ),樂器演奏的技巧勝過一切,但對於整體音樂「性格」的塑造,以及現代爵士樂究竟應邁向何方,如何發展?樂手之間缺乏深度的討論。
有鑑於此,席佛向 Alfred Lion 建議,「藍調之音」應加強五重奏或六重奏編制的錄音,讓主奏樂器(小號、薩克斯風)與節奏組之間保持一種平衡的關係。這也就是說,主奏樂器應在編曲者的控制之下,一方面充分發揮樂器主奏時的魅力,另一方面與團員合奏時,不至於搶了別人的風采,反而透過更緊密地互動,讓整體音色均衡優美。除此之外,席佛也向 Alfred Lion 建議,應讓樂手多作功課,多練習新曲,甚至付錢讓他們可以在錄音前先有幾天的預演,以增強專輯品質。
席佛一席話,創造了十餘年風光的「藍調之聲」,由「爵士信差」和後來席佛帶領的五重奏為首,開枝散葉,拉拔後進不知凡幾,創造了現代爵士樂最輝煌的篇章。莫怪乎當時藍調之音最大的競爭者,另一家獨立的爵士樂廠牌 Prestige 的製作人 Bob Porter 曾經羨慕地說:「藍調之音與 Prestige 最大的不同是兩天的預演。」
席佛的五重奏究竟拉拔了多少樂手呢?從最早的 Hank Mobly 與 Kenny Dorham 搭檔、全盛時期的 Junior Cook 與 Blue Mitchell 、被譽為完美搭檔,才氣縱橫的 Joe Henderson 與 Woody Shaw 、後來在 hard bop 樂派中自成一家的 Clifford Jordan 與 Art Farmer 、晚期的 Becker 兄弟與 Bob Berg 與 Tom Harrell 的組合,個個都在席佛五重奏的羽翼下成長,在爵士樂壇都曾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作為領航者的席佛,究竟如何看待他自己創造的「藍調之聲」過程呢?席佛在六○年後期發行的「 Serenade to A Soul Sister 」內頁說明,曾經列出他的作曲指導原則:
• 旋律之美( Melodic Beauty )
• 意涵豐富的簡單( Meaningful Simplicity )
• 和聲之美( Harmonic Beauty )
• 節奏感( Rhythm )
• 環境的、承傳的、地域的、和靈性層次的影響( Environmental 、 Hereditary 、 Regional 、 and Spiritual Influences )
「旋律之美」、「和聲之美」、「節奏感」是創作天分的指標,無庸贅述。而「環境的、承傳的、地域的、和靈性層次的影響」,則說明了席佛勇於吸收、融合各種不同音樂元素的野心。至於「意涵豐富的簡單」,大概是席佛作品中最顯著的特徵了。席佛的鋼琴彈奏根植於藍調的和弦進行(若是快速地彈奏,就是 Boogie Woogie )與福音詩歌的傳統,讓左手大量地反覆彈奏低音。表面上,席佛低音反覆彈奏的方式似乎簡單,但卻能製造律動性十足的音樂,偶爾神來之筆的鋼琴主奏,其樂句也都較短,卻不失其活潑與躍動感。
類似的精神,也可在「 Doin' the Thing 」這張 Village Gate 的現場專輯聽出端倪。席佛彈奏大量的藍調和弦,左手反覆地敲打低音到一種誇張的地步,伴隨著 Blue Mitchell 或 Junior Cook 吹出的狂野旋律,席佛偶爾以幾段旋律短句予以回應,但更重要的是,那持續反覆的重音所製造出來的舞動與搖擺感,不就是後來以電貝斯和鼓製造出來的放客音樂濫觴嗎?
四十年後重聽這些錄音,不但不覺得老舊落伍,反而倍覺新鮮。樂友若是聆聽了更多不同類型的音樂,對於席佛作品特色的辨識感,也許就能超越對「 Song for My Father 」的刻板印象。反覆聆聽席佛在「藍調之音」發行的專輯,我深深覺得,他的編曲功力與時俱進。勇於吸收各種音樂元素的席佛,對於音樂的概念永遠是創新的。
七○年代之後, Alfred Lion 因健康因素離開藍調之音(轉手初期 Alfred Lion 仍負責管理工作),由 Liberty 唱片公司接手製作,稱霸一時的「藍調之聲」看似即將邁入歷史,但仍留在該廠牌的席佛,七二年錄製的「 In Pursuit of the 27 th Man 」專輯,收錄了多首席佛的個人創作,音樂水準之整齊,令人大為激賞。這張專輯由兩次錄音所組成,年輕的 Brecker 兄弟負責小號與薩克斯風,他們倆在拉丁節奏中,帶出了極為無畏生猛的旋律,而另一次的錄音,則罕見地由 David Freidman 負責演奏電顫琴,悅耳輕盈的音符,與席佛的放客靈魂感互為搭配,作了很好的平衡和潤飾。
「 In Pursuit of the 27 th Man 」專輯用了當時最流行,也是唱片公司為了提升專輯質感的對折封套( gatefold sleeve )。全黑的封面背景中間,穿著「 1 」號球衣與運動短褲的席佛,滿臉落腮鬍,一臉嚴肅,神秘地奔向未來。曾經是藍調之音最重要也是最有市場緣的樂手席佛,穿上這件「 1 」號球衣,稱他為放客爵士 No.1 鋼琴手,絕對是當之無愧的。
Horace Silver
::Silver Serenade::
0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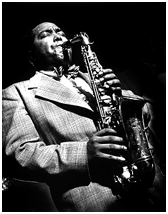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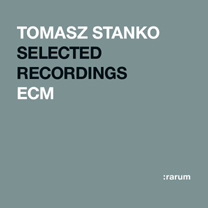
好棒的曲子, 讓我引用成一篇網誌的背景音樂吧~~
回覆刪除會註明出處~
如果覺得不行, 請來信告知.
他奶奶ㄉ
回覆刪除